人类对神经系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基于计算手段的人工智能研究也走过了60年,并已被运作在航天航空、交通运输、临床医学、生物学等多方面领域中。然而“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发展到人类无法驾驭的超级智能阶段”这种忧虑始终存在,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直言,人工智能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将最终控制或毁灭人类。
未来人工智能会如何发展?9月16日,复旦大学“科学与文化”公开课上,进行了多学科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发展探讨。
房间外的人用测试对象理解的语言去询问两个他不能看见的对象任意一串问题,这两个对象一个是正常思维的人,一个是机器。经询问后,房间外的人不能分辨两者的不同,则机器通过“图灵测试”。
房间外的人用测试对象理解的语言去询问两个他不能看见的对象任意一串问题,这两个对象一个是正常思维的人,一个是机器。经询问后,房间外的人不能分辨两者的不同,则机器通过“图灵测试”。
理想远未实现
“以前人们设想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其实还远远没有到实现的地步”,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认知算法模型实验室教授危辉直言。危辉介绍,人工智能最直白、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智慧地工作,机器人秘书、计算机代替心理医生、机器翻译……这些是自人工智能概念提出后,人们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发展预期,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预期无一例外,全都落空。
危辉举例:“机器翻译一度被认为是比较好实现的,只要设计好一本双语对照的电子词典和语言转换规则就够了,把一串字符符号转换成另一串字符符号就可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做到。从1950年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理论奠基人图灵提出‘图灵测试’,至今60年的实践证明,人们大大低估了背景知识在其中的作用,而这些知识可谓无边无际”。

2014年,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
在图灵测试大会上冒充一个13岁乌克兰男孩,通过了图灵测试。
“一个计算三重积分的程序能够解算任意形式的表达式,却可能对于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做的图像识别归类手足无措,只要涉及图像处理、图像理解、归纳推理,以及大量范围不确定的背景知识,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就是很大的挑战”,危辉说这反映出人工智能面临一个深刻的选择题:是选择单打独斗地解决一个个孤立的应用,还是系统全面地探讨智能的本质。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自动驾驶领域,在封闭、单调、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实现匀速驾驶不难,但是让自动驾驶汽车驾驶弯曲、曲折的道路,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挑战。这两个事例有一个共同之处们就是所正对的应用都是存在很大变数或不确定因素的,人工智能想要事事都预先设定好是不可能的,而人的智能恰恰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乔守怡对此也表示认同:“用以图灵机为基本计算模型的计算机来发展人工智能,只是用程序式的方式来模拟人的思考方式。而从生物学角度,人的思维方式是通过神经信号的传导来做,这是不同路线,如果按照图灵机的模式,计算机就算发展得更高级、更精细,恐怕也无法达到人脑的一个简单思维方式”。
中文房间是一个用来反驳强人工智能观点的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对汉语一窍不通的人关在一间只有一个开口的房间中。房间里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手册,指示其如何处理收到的汉语讯息及如何以汉语回复。房外的人不断向房间内递进中文问题,房内的人按照手册说明查找合适指示,组合成对问题的中文解答递出房间。尽管房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汉语,但他却压根不懂汉语。
中文房间是一个用来反驳强人工智能观点的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对汉语一窍不通的人关在一间只有一个开口的房间中。房间里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手册,指示其如何处理收到的汉语讯息及如何以汉语回复。房外的人不断向房间内递进中文问题,房内的人按照手册说明查找合适指示,组合成对问题的中文解答递出房间。尽管房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汉语,但他却压根不懂汉语。
人工智能的现状——灯下亮
显然此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太过理想化,如今人工智能的现状是什么呢?危辉说,一是碎片化,已经研究了许多小分支,但无法统一成体系;二是实用主义倾向:更关心某个机器的实用性,而忽略其科学价值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比如脑电的电极帽,通过脑电信号来控制机械装置运作。
这样的装置有用,但并非如宣传的“能读取人的思想”那样,有些言过其实,并且对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来说作用都有限;三是“灯下亮”,意思是人工智能现在惯常用的技术,是用已有工具来解决好解决的问题,灯没照到的地方依然是大片黑暗;四是“盲人摸象”,人工智能界不同的研究流派理论源头、技术、目标都不相同,各执一词,一切都处于争论之中,能够达成的公式,能够普遍推广的准则少之又少。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将人工智能归为一种技术,而不是一种科学,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现在看似非常繁荣的景象:如打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这些其实不但不能证明我们对智能的理解有多深刻,反而证明我们还很无助,因为我们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分别打造应对不同需求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而人的大脑能够不加准备、不费力气地切换到其中任何一项任务上去,而且只基于一个相同的硬件环境”。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都是极为热门的技术,它们具有异常强大的存储数据的能量和计算能力,那么依靠这些新技术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为人工智能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呢?危辉认为,情况可能也未必如现在想象的那样如意。
“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确能够加速现成算法的运行,但并不能创造新的算法,更何况这两种技术还依赖于非常庞大的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能耗、体积都不小。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够把一些人类智能所不擅长的任务,如精确的海量记忆和密集的数值计算,运行得很好,但依然不能反映人类智能的本质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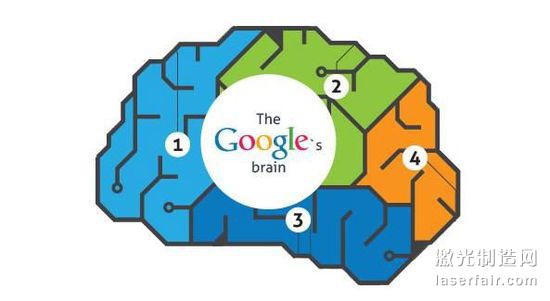
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发出的一款模拟人脑的软件——谷歌大脑。
人工智能的未来在哪里?
虽然由于来自生物学的证据有限,计算机仿真太难和出成果太慢等原因,基于生物机制的人工智能研究依然缓慢,但基于大脑认知机理的人工智能研究一定会成为真正能够突破瓶颈的关键点。
危辉认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出路应该是在生物模拟这条道路上,比如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类脑计算学中找到很好的想法。“神经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计算结构,数学、物理学能告诉我们一些实现方法,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产生和现在计算机完全不同的体系结构,也许类脑计算模型可以把智能做的更好”。
“从狭义角度来说,智能是记忆和预测的系统,比如我们对某件事似曾相识,就会有预判出现。对于人来说,一辈子都在学,都在改变,犯错也是可塑性的表现。而计算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固化的体系是没有生存力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洪波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解读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每个人的脑构成方式都不一样,现在的脑状态和下一分钟的脑状态又不一样,今年你接触了一个新的事物,你的脑构造方式又发生了变化。从人工智能角度,神经元网络最重要,人的意识变化非常快,稍纵即逝。在神经网络上,脑子当中此起彼伏发放的数字电位式的电信号时时刻刻在传递信息”。
俞洪波介绍,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发出的一款模拟人脑的软件——谷歌大脑,科学家们将1.6万台电脑的处理器相连接建造出了全球为数不多的最大中枢网络系统,它能自主学习,通过应用这个神经网络,谷歌的软件能够更准确的识别讲话内容、识别出猫的图片。“既然谷歌大脑能够学会‘猫’这个概念,那么他也可以学会其他概念、可以看图说话”。
基于生物学基础上的人工智能也将造福人类。例如,神经生物学家对高等哺乳动物的生物视觉系统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从视觉信息加工早期阶段的视网膜,到后期阶段视觉中枢的高级皮层区所设计的解剖结构和功能都有了一些认识,那么基于这些原理人们可用开发某些具有实时图像加工能力的数字化芯片。若芯片做得足够小,功耗足够低,生物相容性足够好,生物电信号的衔接协议足够精准,那么就有可能把这样的芯片植入一些有视觉障碍的人士体内,帮助其恢复部分视觉功能。
那么在生物学基础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一片光明了呢?俞洪波表示,他与许多学者一样,保持“审慎的乐观”。“还是‘灯下亮’的概念,我们只研究出了一点点灯下亮的地方,还有太多的不可知区域。你给谷歌大脑上百万张图片让它认识猫,但你给一张狗的照片呢?依然是不认识。这是学习迁移、泛化能力的缺失。我非常认可神经生物学角度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但要意识到我们依然在极其初步的阶段”。
“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确已经到了突破的时代,但仍然很遥远,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模仿人的智能,而这还不涉及到情绪、更谈不上意识”,俞洪波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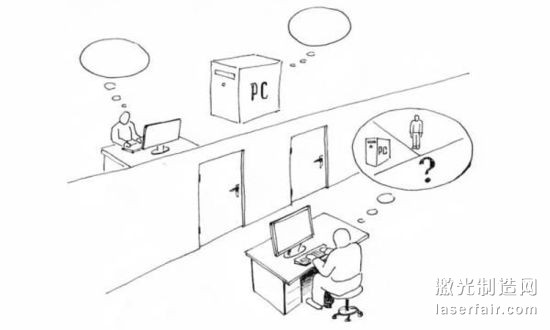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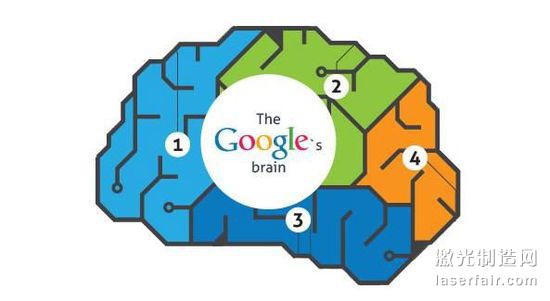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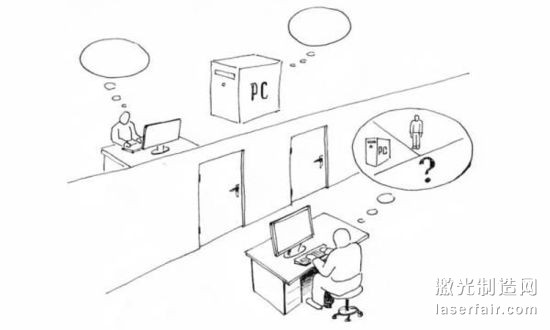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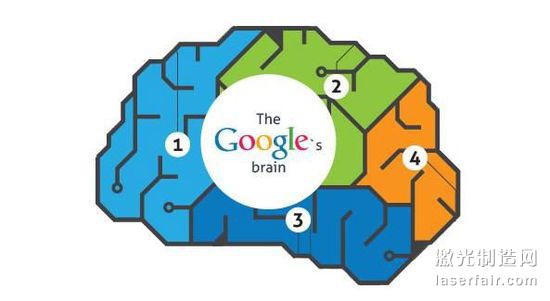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