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学钟兴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闫锋已经磨了一个月。两个月后再见时,发现他依然在磨。钟兴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疑惑,“你堂堂一个博士生磨这个干什么,还磨得那么开心?”
外人或许难以想象,在和那块肉夹馍大小的镜子“软磨硬泡”一年中,闫锋对材料特性、光学制造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加工工艺、轮廓测量、干涉检测等相关技术的理解愈发深入。最终,闫锋“磨”出了一张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的博士学位证书,并如愿留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工作。
2012年,闫锋成为一名新上岗的硕士生导师,并于2013年招到了第一个研究生。
在“多快好省”工业化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大行其道、导师只爱课题不爱学生的大环境里,科教结合异化现象严重,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变成廉价的“学术工人”,更有甚者抱怨“读研原来就是替老板干苦力活儿!”
闫锋无疑是个例外。
让人欣喜的是,笔者近日走访长春光机所时发现,有着类似闫锋经历的并非个案,该所在破解科教结合异化难题道路上已经走出很远。
尊重学生科研兴趣,在实践中激发年轻学生的创造力
长春光机所被誉为中国光学的摇篮,先后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在这里,“工程节点”的概念人尽皆知:一个节点没完成前,所有的工作都会紧张进行。
这也意味着,闫锋干起活儿来并不轻松,偶尔,他甚至用“苦逼”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读研时周六不休息,现在工作了,连周日的概念也没了。”
但他仍自得其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感兴趣”。
“磨镜子”这个题目是闫锋自己挑来的。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读博时,导师向他介绍了所在领域的前沿课题,并给了他若干个科研题目,任他挑选。
相比一些学生被动接受导师“硬塞”的题目,幸运许多。
在闫锋看来,学生有了选择权,产生了兴趣,“就不再是被动地干体力活儿,而是非常有冲劲儿地去探索未知”。
“你想学什么?”
这通常是颜昌翔问学生的第一句话。这位长春光机所空间一部副主任、研究员说,在他的课题组里,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多个领域的课题,如果为了图省事,他大可将所有的工作摊派给学生,但作为过来人的他深知,“把学生逼成了苦力,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既害了学生,也耽误了科学研究。”
人才学家对获奖者的获奖成果统计发现,108名获奖物理学家最佳创造年龄在31岁~35岁,91名获奖化学家的最佳创造年龄在31岁~40岁,102名医学家或生理学家做出最富创造性成果的年龄在36岁~40岁。爱因斯坦甚至说:“在30岁之前没有对科学作出他的最大贡献的人将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贡献。”
强扭的瓜不甜,而顺水推舟,在年轻人创造力最旺盛、对探索未知最渴求的阶段,将他们感兴趣的题目分给他们,将对其个人、导师、研究所乃至中国的基础研究都善莫大焉。这也是长春光机所的做法。
到现在,还有人不能完全理解闫锋的“快乐”。他这样回应,“如果对科研题目没产生一种内心的狂热,稍微苦一点就不会快乐,而我正乐在其中。”
事实上,他耗时一年磨出来的那块镜子在业内还有一个特殊的叫法:国内第一块碳化硅的自由曲面。
当然,真正动手做科研之前,理论基础必须要先打好。
当研究生忽视基础理论课,第一年就被导师拉进实验室干活儿的新闻见诸报端时,长春光机所却为学生设计了贴近科技前沿的各类课程,并聘请国内知名高校老师来所里授课;并设定“红线”,“哪怕是学生在跟随导师一起完成工程项目的时候,也不能落下对前沿理论知识的学习”。
魏群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尽管平时的科研实践任务很重,但导师还是坚持每一周都要在组内举行读书报告会。具体而言,就是要每个学生讲一篇SCI论文,介绍前沿领域的理论创新。尽管听上去简单,但“讲出来和单纯地看懂不一样,除了这一篇文章,还要阅读相关的英文论文5~10篇左右,而且还要接受导师和同学的提问”。
“对年轻的学生来说,他的知识结构尚未建立,甚至连做事的方式方法也未完全学会,导师在这时候要做的就是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循循善诱。”说这话的魏群如今已是长春光机所的一名硕士生导师,还是该所最年轻的实验室副主任。
魏群记得,2005年,他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波给他出过一道题:看一份驱动器的说明书。魏群看完后,导师又让他实地去买一个驱动器,他也照办了,接下来又按照导师要求操作驱动器,向前,向后,都试着完成了,导师又加了几个动作,魏群也都搞定了。最后,导师告诉他,把驱动器放在真空中,将之前做过的动作连续做一遍。
这时,魏群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大题目”,而这一驱动器真正应用是放在探月工程“嫦娥”探测器里面。
“如果一开始导师就告诉我这个题目是什么,我可能一下子就懵了,现在整个过程下来,不仅学会了具体的研究技术,还学会了一套合理的、规范且有效率的做事方法。”魏群说,等他招到学生之后,也像这样教学生。
向最好的老师学习,超过自己的老师
像陈波这样通过言传身教来影响人的老师,被不少学生称作长春光机所最大的财富。
至今,钟兴都记得,在2005年一次座谈会上,正读研究生的他聆听了王大珩先生“手把手教学生”的一段故事。
故事发生在长春光机所成立早期,所内实验器械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都尚未健全。王大珩先生就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甚至在一次会议上,他直接登上讲台,向师生演示在实验室内如何换鞋,“先换哪只后换哪只,做得十分清楚”,边做边讲解其中的要点。
更让这些学生欣喜的是,在长春光机所,他们可以随时挖掘和使用这些“资源”。
吕金光是今年留所的博士生。他还记得,在他攻关一个工程的结构设计时,遇到难题,而这又不是其导师的研究领域,需要求助他人。
他和研究组的其他同学一起抱着笔记本,敲开了长春光机所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韩昌元办公室的门。
不试则已,一试就让他尝到了甜头。 “老先生非常热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以为最多谈个十几分钟,他却主动拉着我们就科学原理、工艺技术讨论了两三个小时。”吕金光说,所里很多老先生都很乐意跟年轻人谈论问题,指导他们学习。
过去,人们总说教会学生饿死师傅,如今,颜昌翔却坚信“在自然科学领域,把学生教会了,自己也一定在进步。”
毫无保留地对待学生,这是颜昌翔自己的一种坚持,在他看来,学生总是需要一些“特殊待遇”的。
15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博士生时,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春光机所原所长王家骐就定了一条规矩,“任何学生进我的办公室,都可以不敲门直接进来”。
颜昌翔记得,一次,他径直走到王家骐院士桌前时,伏案看文章的老先生还没发现,他便叫了一声老师,把王院士吓了一跳。
“学生要在他所研究的领域比导师还要强,才能说这个学生教得合格了。”长春光机所空间二部主任、研究员韩诚山说。
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一句大话。
在长春光机所,有种说法是要“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工程师”,韩诚山自谦是一名工程师,更擅长解决工程问题,把一个科学想法变成现实,而对“为何能实现”等科学理论问题他也非常重视,而且鼓励富有活力的学生去做研究,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去和学生“交流沟通”。
韩诚山从不回避一个现实问题,身为导师,通常会被科技会议、工程项目占用大量时间,但即使再忙,也“不让学生替自己‘没时间’,或是为完成工程而去做一些纯劳动性的工作”。
他说,这是底线。
在科学界,还流传着著名光学家蒋筑英求学长春光机所的故事。1962年,时年23岁的他写信说服母亲,从北京大学考入长春光机所,成为王大珩的研究生。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节目。
迈入21世纪,这种实践中培养高质量学生的做法,也为长春光机所吸引来诸多优质生源。一个非常喜人的数字是,在该所近年来的生源中,985高校学生可占80%以上。
魏群说,当一些学生在抱怨自己在逼仄的实验室里当着“学术工人”的时候,他正在和导师讨论着实践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当一些人抱怨,今天导师又硬塞给自己一个题目做时,他却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所在的环境,究竟怎么看待学生,是培养你,还是单纯地利用你?”
带学生不行一票否决,取消导师招生资格
如何界定导师的权限,国科大在尝试给出一个令学生满意的答案。
2012年7月,国科大正式更名,作为一所依托于中科院110余个研究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就是要为各研究所打造一个教育平台和管理框架,让研究所“回归到教育功能原位”,成为中科院“研究生培养中真正的‘院系’”。
“从制度上对导师的权力设置‘边界’,比如学生可以在理由正当的前提下经许可更换导师,而原导师不需签字。”在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如是说,“北京大学有蔡元培学院,南京大学有匡亚明学院,国科大为什么不能办几个黄昆学院、(王)大珩学院、(竺)可桢学院呢?”
这一设想已经成为现实。2013年7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大珩学院在长春光机所揭牌成立。
肩负“大珩学院”这一光荣头衔的长春光机所早就开始推行“导师组”培养模式。所谓导师组,就是学生除了自己的导师之外,还有若干不同科研方向的副导师。这种“多对一”的培养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快速学习各种学科知识和技能,更能营造出一种开放、平等、教学相长的学习气氛,让同学和老师坦诚交流、共同进步。
建章立制,是破解导师只爱科研不爱教学难题的第一步。
笔者看到,对于长春光机所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至少已完整培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协助指导过博士生,且培养质量较好。”
翻看该所《博士生导师评价体系》,其内容则更为实在。
针对“导师责任心”这一看似较虚的考核项,却通过多个节点和具体分数的打分来夯实,比如:开题报告前导师应检查和指导修改开题报告、组织学生进行组内预报告,导师得10分,做论文期间每名研究生只能改一次论文题目,但是,改论文题目1次,扣除5分。
颜昌翔告诉笔者,这一考核方式通常是靠研究生部来监督,“老师要将学生原始开题报告(保留导师修改痕迹)、修改后开题报告、预报告‘签到表’都交给研究生部作为赋分凭证,审核备案。”
在学生的选题方面,导师也要充分尊重学生的科研兴趣。颜昌翔谈到,他通常都会给学生几个研究方向,让他选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深入下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能否让那些乐于坐冷板凳的学生,坐得住,坐得值,就看导师的水平,尤其是用心与否了。
一条有意思的规定是,教书育人附加分办法,即学生获得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院级奖励,导师加20分,而学生一旦有无故迟到、早退、旷勤的情况,则要扣导师5分。
有学生开玩笑说,这种“连坐捆绑式”的考核办法不得不让导师开始留意自己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
最为关键的是,这条考核体系涉及了具体实施条款。其中导师考核标准及待遇一项提到——
对于考核合格的导师可以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简章,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导师将不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简章,(两年内)停止招生。
对于连续3年没有招到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将不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简章。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导师,如需要再进入招生简章恢复招生,需本人提出申请,由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再进入招生简章恢复招生。
长春光机所在师生比上也作了制度上的规定:每名导师原则上每年最多可招收博士生两名,但对于有博士毕业生的导师(或协助培养导师),当年分数超过合格分数的导师,下一年度可增加1个招生指标。
破解科教结合难题,需回归人才培养规律
破解科教结合异化难题并非一蹴而就。
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中同样普遍存在,上个世纪末,国际高等教育界就有人发出警告,“科研赞助成为指导和潜在的合作中介,教授变成项目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学生被以命令的方式进行指导,被像雇员和技术员那样对待”,“学生为教授学术晋升而受剥削,历史上是以大学科研制度为基础的”,最重要的是,“科研和教学,一般很少谈到学生的参与,学习的成分很容易被忽略”。为此,有人大声疾呼“传统上为知识而生产知识和对未来几代科学家和学者进行有效的训练的大学,必须作出补偿性的行动”。以理论课学习为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基础课程学习非但不能削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用韩诚山的话来说,“爱迪生一个一个试,试了上万个,才把钨丝试了出来,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但如果可以从理论上进行一些探索,没准儿就更有效率。”#p#分页标题#e#
然而,冷冰冰的现实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只注重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工作,不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
“这是导师职责认识的缺憾!”白春礼曾直言。
对中科院的研究生教育来说,其优势就在于科教融合,学生在跟随导师从事高水平科研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即作为学生的小鱼,“从游”于作为大鱼的老师。
然而,就在学生和导师的角色双双发生变化之时,在科研院所里的学生,很容易被异化成“职工”,即所谓的科研助手。
如果学生本人心理错位成了职工角色,就会心态不平衡;导师会以分配科研任务为主,而对学生的困惑不闻不问;研究所的园区建设常常忽略学生文体活动的需求,甚至于学生即使出现问题,也从不问自己是否已尽了育人之责。
“如果回归到人才培养规律,怎么办就一目了然。”长春光机所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所长张涛说。
事实上,在一线的科研和教学单位里,有关“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的讨论并未停止,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人,是社会各个岗位中坚力量的人,是社会个别领域专业短缺的人才?等等,莫衷一是。
但至少有一点,张涛和自己的同事已经达成共识,即长春光机所作为国科大大珩学院,不仅是为所里,更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这才是一所大学应有的责任。
美国大学协会研究生教育委员会(AAU)1998年发表《大学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责任》报告,提出了“学生兴趣优先,最终目的是为研究生而进行的教育,大学行政管理者和教师必须以学生利益为重。助研和助教在某些方面具有雇佣关系,本质上还是学生;不应违背学生的兴趣和职业目标,不应转过来满足教师的研究目的”。
教育重在过程,科研重在结果。
“在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题中,成功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便实验失败了,也可以收获经验。”张涛说,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科研项目,把这样的认知和思考方式烙在学生脑海里,他们将来才有竞争力。
破题,对国科大的研究生教育而言,除了像长春光机所单独探索之外,一个整体上布局或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国科大在更名后的一年多里,已经着手开始了科教融合的创新尝试。除了大珩学院,国科大还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设立了深圳先进技术学院;依托中科院昆明分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设立了昆明生命科学学院;依托中科院微电子所、半导体所等中科院内与微电子相关的研究所,建立了微电子学院。这些依托于中科院各研究所设立的专业学院整合了学科优势资源,提升了学生整体培养水平。同时,国科大在校部设立了10个基础学院,聘请李国杰、康乐等知名院士任学院院长,由各研究所的学术专家组成院务委员会、学科群学位委员会等,统筹规划设计课程体系及学生培养基本要求,形成从校部到研究所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网络。目前,基础学院与专业学院都在结合各自学科的特点,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60多年前,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中科院仪器馆在王大珩、龚祖同、张作梅、蒋筑英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其间,为社会输送了2200多名专业人才和22位院士。
如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身兼“国科大大珩学院”的长春光机所能否真正破解科教结合异化难题,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学院,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拭目以待。
延伸阅读: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建于1952年,主要从事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仪器的研发生产。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长春光机所在以王大珩院士、徐叙瑢院士等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的带领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等多种先进仪器设备,创造了十几项“中国第一”;取得了1700多项科研成果,获专利授权750多项;有22位在本所工作过的优秀科学家当选为两院院士;先后参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长春光机所在科研领域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取得了以“神舟五号”、“神舟六号”、“风云三号”、“天宫一号”有效载荷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研成果。长春光机所已成为我国高级航天光学遥感器、机载光电平台及大型光测装备的主要研制、生产基地。
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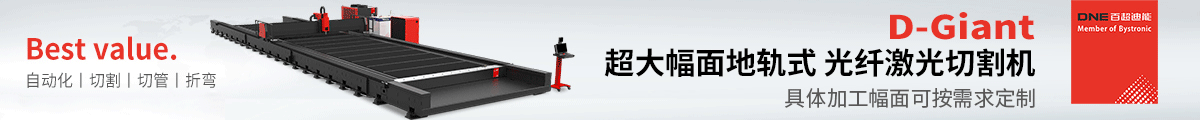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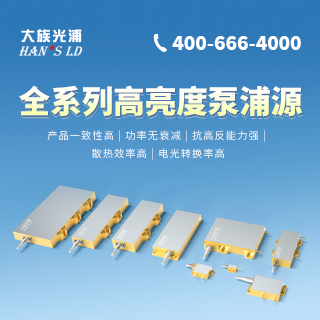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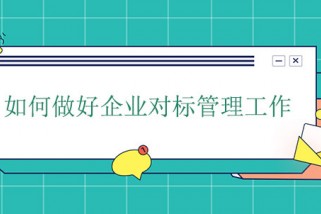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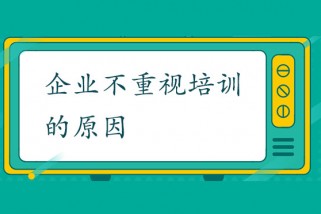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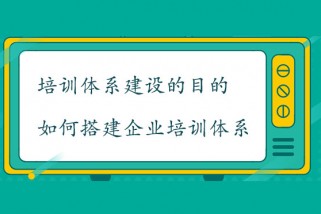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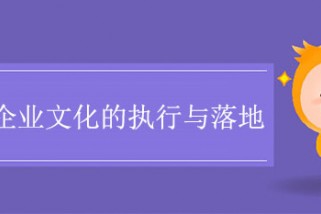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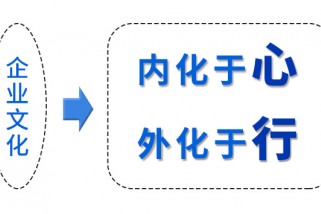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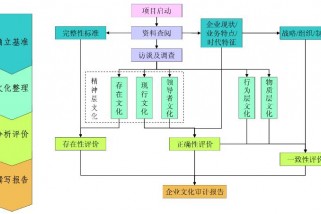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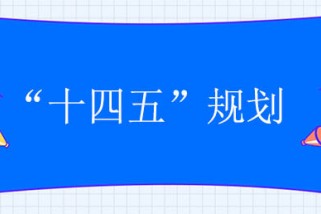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